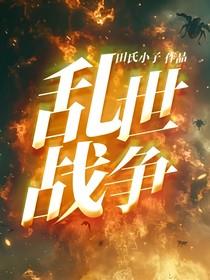第17章:风雨前的部署
第17章:风雨前的部署
第1节:布防图的最后一块拼图
密道里的油灯忽明忽暗,将三张紧蹙的脸庞照得忽隐忽现。赵山河刚钻进洞口,就看见李百晓正用柴刀在石壁上划着什么,孙敬之则蹲在一旁,手里摊着那张被无数人守护过的布防图,边角已经磨得发毛。
“你可来了。”李百晓的柴刀停在“鹰嘴崖”的位置,“刚收到消息,日军在黑石关的暗哨又加了两个,就在涵洞左侧的老槐树下,换岗时间是亥时三刻。”他往赵山河手里塞了半截炭笔,“快补上,这是最后一块拼图了。”
赵山河的指尖在布防图上滑动,找到涵洞的位置。那里已经标注了日军的明哨、巡逻路线、军火库位置,只差这两个新添的暗哨。他握紧炭笔,在老槐树的位置画了两个小黑点,又在旁边标注“亥时三刻换岗”,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像在为大战倒计时。
“这样就全了。”孙敬之的手指抚过完整的布防图,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从密道入口到涵洞出口,从日军的明哨到暗哨,从巡逻队的路线到换岗的间隙,一点不差。”他往图中央的“黑石关”三个字上重重画了个红圈,“皮司令的主攻路线,就定在这里。”
赵山河看着那个红圈,突然想起皮司令将军在根据地沙盘前的模样。当时将军用红笔圈住黑石关,说:“这里是日军的咽喉,卡住了,豫西的主动权就到了咱们手里。”此刻这红圈落在布防图上,仿佛带着将军的体温,烫得人心里发颤。
“夜校的三十个学员已经分到了位置,”李百晓往石壁上的刻痕里塞了根火把,火光瞬间亮了许多,“王二柱带五个人守密道入口,防止日军抄后路;春杏带女眷负责传递消息,她们熟悉各村的小路;剩下的人跟着我,在鹰嘴崖接应皮司令的主力。”
“秉礼学校的残余力量,”孙敬之补充道,声音里带着对牺牲同志的怀念,“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们会在日军后方制造混乱,烧仓库,剪电线,让鬼子首尾不能相顾。”他将布防图小心翼翼地折成方块,塞进贴身的布袋,“这图,我会亲自交到皮司令手里。”
密道深处传来滴水的声音,“嗒,嗒,嗒”,像在为他们的计划计时。赵山河望着布防图上密密麻麻的标注,突然觉得这张纸不再只是情报,而是无数人的心血——孙敬之的粉笔灰,李百晓的柴刀痕,王老汉的玉米地,柱子的牛棚……每一笔都浸着血与泪。
“就等皮司令一声令下。”李百晓的柴刀在掌心转了半圈,铜环撞出清脆的响,在寂静的密道里格外振奋人心。
赵山河的手按在布防图所在的位置,能感觉到那方块的形状,像块沉甸甸的责任。他知道,从这一刻起,所有的暗号、所有的默契、所有的牺牲,都将凝聚在这张图上,化作刺破黑暗的利刃。
火把的光在三人脸上跳动,映出他们紧抿的嘴唇和坚定的眼神。密道外的风越来越急,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奏响序曲。
第2节:军民的誓言
五岳庙的院子里,铁器摩擦的“嚯嚯”声撞在墙上,又弹回来,混着夜风吹动幡旗的哗啦声,像支即将吹响的号角。赵山河刚走进庙门,就被一阵热浪裹住——三十多个夜校学员围着石碾,正磨着手里的家伙:锄头的刃口被磨得发亮,锛子的尖角闪着冷光,连平时挑水的扁担都被削出了斜尖。
“再加把劲!”王二柱光着膀子,古铜色的脊梁上渗着汗珠,他正用磨石蹭着爹留下的锄头,刃口已经能照出人影,“等会儿让鬼子尝尝咱这‘铁家伙’的厉害!”他爹王老汉牺牲时,手里还攥着这把锄头,此刻锄柄上的血痕早已发黑,却像道催征的烙印。
李百晓突然从神龛后走出来,手里的砍柴刀在月光下泛着青辉。他跃上供桌,柴刀往石碾上一剁,“当”的一声脆响,所有的摩擦声瞬间停了。“弟兄们,”他的声音像庙前的古槐,粗粝却挺拔,“皮司令说了,军民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学员们的呼吸突然变得粗重,有人攥紧了工具,指节发白;有人往地上啐了口唾沫,眼里燃着怒火——那是被日军烧毁家园、夺走亲人的恨。赵山河看见最年长的张老汉,正用布条缠着锛子的木柄,他的儿子去年被抓去修炮楼,至今生死未卜。
“咱这密道,”李百晓的柴刀指向神像底座下的洞口,“就是给鬼子挖的坟墓!”他从供桌上跳下来,挨个儿拍着学员的肩膀,“等皮司令的主力一到,咱就从密道钻出去,抄他们的后路!锄头能种地,也能砸碎鬼子的脑壳;锛子能凿石头,也能撬开他们的炮楼!”
“对!砸他娘的!”有人爆发出粗吼,接着是一片响应的呐喊,震得庙顶的瓦片簌簌掉灰。赵山河的手按在腰间的枪上,枪身的温度混着学员们的热血,在心里烧得滚烫——这就是皮司令说的“老百姓的力量”,平时是沉默的黄土,怒时能成掀天的巨浪。
“来,拿着。”春杏突然从厢房走出来,怀里抱着个竹篮,里面摆满了“礼”字香囊,靛蓝的丝线在月光下泛着柔光。她挨个儿往学员手里塞,指尖触到王二柱的锄头时,轻轻顿了顿,“这是跟皮司令的队伍认亲的记号。”
赵山河接过香囊,指尖抚过上面的针脚——春杏特意在“礼”字的右下角绣了个极小的星,跟皮司令部队的标记一样。“见着戴这香囊的,”春杏的声音软却坚定,辫梢的红头绳扫过学员的手背,“就是自己人,别客气!”
张老汉把香囊系在锛子柄上,粗糙的手指在“礼”字上蹭了蹭:“俺孙子说,这字念‘礼’,是‘守规矩’的意思。咱守的规矩,就是把鬼子赶出咱豫西!”他举起锛子往石碾上一磕,火星溅在地上,像撒了把火种。
李百晓突然举起砍柴刀,刀尖指向黑石关的方向:“都记好了!等会儿听我号令,密道里见真章!”他的刀在月光里划了道弧线,“让鬼子看看,咱老百姓的家伙什,比他们的洋枪洋炮更硬气!”
“好!”
三十多声呐喊撞在一起,冲出庙门,撞在远处日军岗楼的探照灯上,仿佛要把那冰冷的光柱撞碎。赵山河望着这群攥紧农具的汉子,望着春杏眼里闪烁的光,突然明白“军民一心”从来不是句空话——它是磨亮的锄头,是绣好的香囊,是无数人在绝境里攥紧的拳头。
夜风卷着香火的味道扑过来,赵山河将香囊塞进怀里,那里贴着布防图的位置,暖得像揣了团火。
第3节:炮声渐近
“轰隆——!”
第一声炮响炸在西村的上空时,赵山河正蹲在秉礼学校的断墙后。砖石的碎屑从头顶簌簌落下,砸在他的草帽上,带着硝烟的呛味。他扒开墙缝往外看,只见黑压压的日军正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围过来,钢盔在夕阳下泛着冷光,像群爬向猎物的蚂蚁。
“赵先生!”春杏的声音从断墙另一侧传来,带着喘息,“日军主力来了,少说有一个中队!”她的辫梢沾着草屑,显然是从玉米地钻过来的,“李叔让我问,布防图……送不送?”
赵山河的手猛地摸向怀里的布防图。那是张用桑皮纸绘的复制品,原件已经让孙敬之藏进了密道暗格,这张复制品上,每处日军暗哨、每条密道路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是皮司令主力伏击的关键。他往日军的方向瞥了眼,炮口的火光又亮了一下,第二声炮响接踵而至,震得断墙都在颤抖。
“必须送。”赵山河从墙后拖出根竹筒,是平时装毛笔的,内壁缠着油纸。他小心翼翼地将布防图卷成细条,塞进竹筒,用蜡封好口,“告诉李百晓,从鹰嘴崖的密道走,那里日军布防最松,务必亲手交到皮司令手里。”
春杏的手在发抖,接过竹筒时,指尖触到蜡封的温度:“俺这就去!”她转身要走,却被赵山河拉住。
“等等。”他解下腰间的“礼”字校徽,塞进春杏的袖管,“要是遇到自己人,就亮这个。”校徽的银质边缘硌着皮肤,“记住,图在人在,人不在……”
“俺懂!”春杏突然提高声音,辫梢的红头绳甩了甩,“俺哥柱子说过,重要的东西,得用命护着。”她攥紧竹筒往断墙的缺口跑,布鞋踩在碎石上,发出“噔噔”的响,像在跟炮声赛跑。
赵山河望着她消失在玉米地的背影,突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李百晓不知何时来了,柴刀别在腰后,手里攥着颗石雷,引信已经露出半截。“我替春杏去。”他往竹筒里看了眼,蜡封的口子严丝合缝,“那丫头年纪小,遇到日军巡逻队容易慌。”
“你熟悉密道。”赵山河把竹筒塞进他手里,“比谁都合适。”他往日军的方向指了指,“我带剩下的人在这儿牵制,尽量给你争取时间。”远处的炮声越来越密,村东头已经燃起了火光,是日军在放火烧房。
李百晓攥紧竹筒,指节泛白。他突然往赵山河肩上拍了拍,力道大得像在传递什么承诺:“放心,就算拼了这条命,我也把图送到。”他转身往玉米地钻,柴刀的铜环擦过裤腿,发出轻响,“告诉弟兄们,等我信号!”
赵山河看着他的身影没入青纱帐,玉米叶在他身后合拢,像从未有人经过。炮声还在继续,震得大地微微发颤,日军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已经能听见他们用生硬的中文嘶吼:“缴枪不杀!”
他从断墙后摸出颗手榴弹,是上次伏击伪军缴获的,弦还没拉。赵山河的目光扫过秉礼学校的废墟,孙敬之牺牲的讲台还在,黑板上的“礼”字被炮弹炸去了一半,却仍能看清那笔挺的竖画。
“孙先生,”赵山河低声说,声音被炮声吞没,“咱们的仗,快打赢了。”
远处的玉米地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赵山河知道,那是李百晓带着布防图,带着所有人的希望,奔向皮司令的方向。而他要做的,就是在这里,用血肉之躯,为那竹筒里的“胜利”,多争取一刻时间。
炮口的火光又亮了,这一次,离断墙更近了。
第一卷完
巩县烽火抗日之豫西铁血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第3次世界大战假想
- 本文介绍是第3次世界大战。
- 0.0万字9个月前
- 特种兵学校:jh(剑华)
- 华灯初上,华山论剑,为你而为,战友情深似海,可是,他对他,还只是战友情吗?而是……CP:剑华,霹蓝,梅灵,啄绿,东燕,瀚音,酸利,北啸,木白......
- 4.9万字7个月前
- 乱世战争
- 独孤林浩是以作者为原型没有固定主角每一章都有一堆主角一章分20回
- 0.7万字5个月前
- 边疆那棵松
- 给予此书致敬中国边防部队,致敬最伟大的人民子弟兵,致敬那些最可爱的人。
- 2.3万字5个月前
- 剧本:黑红(AI改编)
- 罗希万与陈浩在战场上负重伤,被收尸的百姓巧妙救出,二人与游击队幸存者赵永德一起劫得国军军火,秘密组建了自卫队,打黑除恶,先后与保安队、狱......
- 10.0万字4个月前
- 破茧:少年特种兵的荣耀征途
- 这是一部热血沸腾的军事小说,将带你领略紧张刺激的战斗场面,感受团队协作的力量,见证青春在战火中绽放的光芒,体会军人保家卫国的崇高使命感。
- 3.4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