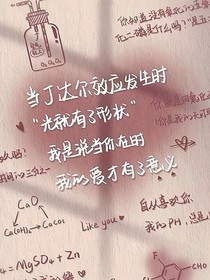第19章 红绳记粮
第19章 红绳记粮
第1节:农民的账本
夜校的梁上挂着串红绳,在油灯下晃悠,像串吊着的火苗。赵山河仰头数着,一共四十六个结,每个结都被攥得紧实,绳头磨出了白絮——这是近半个月各村被抢的粮数,按李百晓说的,“一个结,就是一百斤血汗”。
“赵同志你看。”蹲在梁下的二柱突然举手,手里举着根新红绳,“俺村今天又被拉走两车,这是刚打的结。”他的指关节肿着,是前几天拦粮车时被日军枪托砸的,红绳在他手里晃,像条要咬人的小蛇。
李百晓站在灶台边,正把红绳结记在麻纸上。他的毛笔杆裂了道缝,蘸墨时总往下滴,在“河西村”三个字旁边晕出个黑团。“记清楚了,二柱。”他头也不抬,“皮司令说,知道鬼子抢了多少,才能算清该炸掉多少仓库——他们抢四十万斤,咱就掀了他们能囤五十万斤的窝。”
赵山河的手按在怀里的账本上——那是孙敬之送来的官方记录,县维持会的人盯着他记的,本该掺着水分。可他翻到“河西村”那页,孙敬之写的“两千斤”,竟和梁上红绳的两个结分毫不差。他指尖划过纸页上的折痕,孙敬之送账本时说“这数是老百姓堵着门逼我记的”,当时只当是应付,现在才懂——这哪是账本,是拿命攒的证据。
“李先生,”有个老婆婆颤巍巍摸进来,手里攥着根红绳,绳头缠着片干玉米叶,“俺家存的种子粮被搜走了,就三斤……能算个结不?”
李百晓立刻放下笔,接过红绳系在梁上,打了个极小的结。“咋不算?”他声音放软了些,“种子是明年的指望,比成粮金贵。这结我做个记号,皮司令看了就懂。”
老婆婆抹了把眼角,袖口沾着麦糠:“俺男人说,当年皮司令的兵路过,借了俺家两升米,临走留了块银元,说‘老百姓的粮,一粒都不能白拿’。现在鬼子抢咱的,总有算清的那天。”
赵山河看着那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结,突然发现梁尾还有个单独的红绳,没和其他绳串在一起,结打得特别紧,绳芯都露出来了。“那是?”
李百晓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突然把油灯往灶膛边挪了挪,阴影遮住了半张脸:“是王铁匠的。他给鬼子修枪时,偷偷记下了粮仓的铁锁型号,昨天被发现了……”他顿了顿,手指摩挲着毛笔裂缝,“这结代表他藏的锁钥图,算一千斤——他说,一张图能换万石粮。”
正说着,院外突然传来狗叫,是村里的老黄狗,平时只在日军来了才会这么叫。二柱猛地吹灭油灯,梁上的红绳在黑暗里只剩模糊的轮廓。赵山河摸向短刀时,听见李百晓在他耳边说:“红绳都记在心里了?要是梁被烧了,咱就得用骨头刻账。”
黑暗中,那根单独的红绳突然晃了晃,像是被风刮的。可密不透风的屋里,哪来的风?赵山河眯起眼,隐约看见绳头垂着个东西,不是玉米叶,倒像是片带着齿痕的布——像日军军服上的布料。
第2节:货郎的情报网
赵山河的指尖刚触到货郎腰间的“晓”字令牌,就被对方攥住了手腕。那是个穿蓝布短打的后生,指节上缠着圈黑布条,勒得太紧,渗着点暗红——像是刚被日军的刺刀划破的。“赵同志?”后生的声音压在喉咙里,带着气音,“李先生说你要验令牌,得先看背面。”
赵山河低头,令牌背面刻着道极浅的竖痕,是皮司令部队特有的暗号标记。他刚松开手,后生突然往他手里塞了个油布包,触手硬邦邦的,裹着棱角——拆开一看,是块烤焦的玉米饼,饼芯嵌着张油纸,画着三个圈,每个圈旁都标着时辰。
“这是城西粮仓的换岗时间。”李百晓端着碗粗瓷茶走过来,茶沫子在碗沿晃,“老周昨天扮成收破烂的,蹲在粮仓后墙根啃了三顿干馍,才数清鬼子换岗的间隔——每次换岗有三分钟空隙,墙根第三块砖是松的。”
赵山河捏着油纸边角,纸面还带着玉米饼的焦香。他抬眼时,看见院里又进来三个货郎:挑着货担的老汉竹筐里摆着针头线脑,却在弯腰时露出筐底的铁条——是用来丈量粮仓高度的;挎着布包的妇人手里摇着拨浪鼓,鼓腔里塞着团棉絮,拆开竟是日军军装的布料,绣着番号;还有个瘸腿的后生,货担上的糖人捏得歪歪扭扭,糖人肚子里却藏着根细竹管,倒出来的粉末在桌上拼出“今夜运粮”四个字。
“都是皮司令教的法子。”李百晓用手指敲了敲桌沿,“他说‘流动哨要像田埂上的草,看着普通,根却扎得深’。”他突然朝挑担老汉使了个眼色,老汉立刻从货筐底层翻出个账本,纸页边缘卷得发脆,上面用朱砂画着红绳——和夜校梁上的红绳结数一模一样。
“孙敬之的官方账册,是给鬼子看的。”老汉用袖口擦了擦账本上的灰,“咱这账,是给皮司令算的实账。你看这页——”他指着“南坡村”三个字,旁边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粮仓,“鬼子说抢了五千斤,其实是八千,那三千藏在村西的枯井里,咱用红绳多打了三个结,货郎路过时就顺道报给游击队了。”
赵山河正翻到“河湾镇”那页,突然顿住——纸上画着个粮仓,旁边标着个“?”,红绳结却打了七个。“这是?”
“是王货郎没回来。”妇人突然开口,拨浪鼓的木柄被她攥出了汗,“他上回说河湾镇的粮仓加了岗,得再探探。可前天该回来的日子,只在镇上的老槐树下找到这个。”她从布包里摸出半截红绳,绳头缠着片日军的臂章布料,边缘有齿痕,像是被人临死前攥过。
李百晓把半截红绳系在账本上,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按皮司令的规矩,没回来的人,账上留个‘?’,红绳照记——等把鬼子打跑了,咱拿着红绳去他家报数,就说‘你男人记的账,咱算清了’。”
这时院外传来“叮铃”声,是货郎的铜铃。挑担老汉突然绷紧脊背:“是老陈,他负责的东仓库今天该有信。”可铜铃声越来越近,却带着种奇怪的拖沓——像是货担被什么东西拖着,铃舌撞得七零八落。
赵山河摸向腰间的短刀,听见李百晓在他耳边说:“老陈的铜铃是新换的,声脆,不会这么闷。”他抬头时,看见院门口探进个脑袋,是老陈没错,可他的货担歪在肩上,半边蓝布衫浸在泥里,嘴角淌着血——看见院里的人,老陈突然张大嘴,却没发出声音,只朝着账本的方向,手指痉挛似的弯了弯。
赵山河的后颈猛地发僵。老陈的手指弯成了“三”的形状——是皮司令部队的“危险”暗号。而他货担里露出来的,不是往常的杂货,是件日军的军大衣,衣角还沾着新鲜的红绳碎屑。
第3节:日军的嗅觉
老陈被李百晓拖进柴房时,嘴里还在往外冒血沫。赵山河按住他的后颈,摸到块硬邦邦的东西——是颗子弹,卡在肩胛骨缝里,衣料被烫出个焦洞,散着股火药和血腥味。“说。”他攥着老陈的手腕,感觉对方的脉搏像惊惶的兔子,“是不是被盯上了?”
老陈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响,突然拽住赵山河的袖口,往他手心里塞了个东西——是粒被牙齿咬得发扁的玉米,玉米粒上刻着道竖痕,和货郎令牌背面的标记一样。“东仓库……换了新少佐。”他的声音劈得像被扯断的麻绳,“他让伪军查货郎的货担,说‘中国人的货郎,比狗鼻子还灵’。”
柴房的门被风撞得“哐当”响,李百晓正蹲在灶台边削锄头柄。他手里的凿子凿得飞快,木屑簌簌落在地上,混着灶膛里的草木灰。“皮司令上个月就说过,‘鬼子要是盯紧了一条路,就得换条道走’。”他把凿空的锄头柄递过来,里面藏着卷油纸,“让货郎别再卖杂货,改卖农具——锄头、镰刀、木犁,越像给地里干活的,越安全。”
赵山河捏着锄头柄,触感粗糙,带着新木的腥气。他往院里看,挑担老汉正把刚收到的粮仓草图卷成细条,塞进镰刀的木柄里,边塞边念叨:“这镰刀是王铁匠打的,柄里的缝他特意留宽了三分,说‘装得下情报,也装得下咱的骨气’。”那妇人则把日军换岗时间写在桑皮纸上,裹进刚烙的玉米饼里,饼香混着墨香飘过来,竟压过了柴房里的血腥味。
“赵同志你看。”李百晓突然指向院角的石磨,“老陈刚才塞给你的玉米,得磨成粉。”他往磨盘里倒了把玉米粒,转着磨杆说,“新少佐是个细人,听说连货郎的鞋底都要敲敲,可他不会啃玉米饼,更不会磨玉米——这就是皮司令说的‘藏在眼皮子底下最安全’。”
磨盘转得“咯吱”响,金黄的玉米粉簌簌落在竹筛里。赵山河盯着粉里那颗刻着竖痕的玉米,突然听见街口传来“八嘎”的呵斥声——是日军的声音,离得极近,像是已经到了巷口。他猛地按住磨杆,看见挑担老汉的货担还在院门口,竹筐里的锄头柄没来得及藏好,露出半寸油纸边。
“快!”李百晓拽着他往柴房躲,“让二柱把货担挑到后巷,就说去给张大户送农具。”可二柱刚挑起担子,巷口就传来皮鞋踩石子的“咔嗒”声,越来越近,混着伪军的吆喝:“所有挑担的都站住!少佐要查农具!”
赵山河摸出短刀,指尖在刀鞘上蹭出细响。他看见李百晓突然抓起灶台上的玉米饼,往二柱手里塞:“就说给大户送新烙的饼,顺带捎农具——记住,饼要咬一口,越像赶路的样子越好。”二柱咬了口饼,饼渣掉在衣襟上,他刚要擦,李百晓按住他的手:“别擦,就这么去。”
二柱挑着担子走出院门时,赵山河听见日军的皮鞋声停在了巷口。他从柴房的缝隙往外看,看见个戴白手套的日军少佐,正用手杖拨弄二柱的货担——那根藏着情报的锄头柄,就在货担最上面。少佐的白手套擦过锄头柄,突然停住了。
风卷着玉米粉从磨盘里飘出来,迷了赵山河的眼。他看见二柱的喉结飞快地动了动,手里的玉米饼捏得变了形——而那少佐,正弯腰凑近锄头柄,像是闻到了什么。
巩县烽火抗日之豫西铁血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特种兵学校全部cp
- Cp全是cp,都是甜文有一虐文
- 0.5万字7个月前
- 寒海之上
- 传说英勇的战士死后,灵魂回进入英灵殿。而面对自己的杀父仇人,韩勇却下不去手………“和我决斗吧!!!”韩勇递过刀去………
- 0.6万字7个月前
- 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鞘明月照曼心
- 牺牲的烈士是永恒的!
- 1.3万字6个月前
- 决战河山1
- 国难当头,出身于显赫富贵商会之家的川军中尉吴德庆从黄埔军校毕业,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投身于民族解放的铁血洪流之中。作为中尉连长,他以......
- 35.9万字4个月前
- 亚矩阵
- 一个工业集团控制了国家,他想通过脑机控制全人类,在脑机发明者失踪后,一个失意的少年加入到了“矩阵”
- 0.1万字4个月前
- 新秩序——1947(2)
- 简介正在更新
- 1.1万字1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