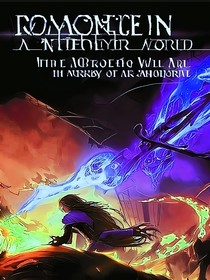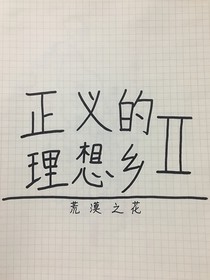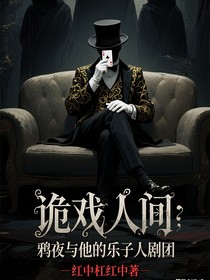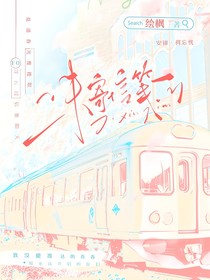第八章:古寺的晨钟
寅时的露水打湿了古寺的青石板,令秋踩着苔痕走近时,听见钟楼传来隐约的钟鸣。那声音很轻,像是从千年的时光里飘来,混着檐角铜铃的脆响,在空荡的寺院里打着旋。山门的朱漆早已剥落,门楣上的“兴国寺”三个字被风雨浸得发黑,却仍透着股庄严的静气。
“王,”令秋从怀中取出往生簿,泛黄的纸页在晨雾里微微颤动,“慧能大师,法号了尘,男,六十七岁,圆寂于唐开元二十三年。在此寺修行四十五年,临终前还在抄录《金刚经》,圆寂时恰逢山洪暴发,为护寺中藏经阁,坐化于阁楼门前。魂魄被他常敲的那口青铜钟缚着,每逢初一十五,就会准时敲响晨钟,至今已有一千二百九十年。”
南川立在大雄宝殿的石阶上,玄色衣袍下摆绣着的幽冥纹在月光下泛着冷光。他望着钟楼的方向——那口青铜钟悬在半朽的木架上,钟身刻满梵文,边缘有处明显的凹陷,像是被重物撞击过。周遭的阴气到了这里,竟都变得温顺起来,连风中的戾气都被晨钟的余韵涤荡干净。
“是哪方的阴差,敢在佛前喧哗?”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钟楼传来,随后,一个穿着灰色僧袍的身影缓缓走下楼梯。他手持念珠,眉目慈和,虽已是魂魄之身,却自带一股安定人心的气场,与寻常游魂的阴冷截然不同。
“了尘大师,”令秋将魂灯往身前送了送,暖黄的光晕在青石板上铺开,“您已在此地守了一千二百九十年。开元二十三年那场山洪,您用肉身护住的藏经阁,至今仍在。寺里的僧人说,每逢您的忌日,阁门前的石阶都会开出白色的苔花。”
了尘大师的目光落在那口青铜钟上,指尖的念珠转得愈发急促:“那年的雨太大了……藏经阁的梁柱都泡软了……我这把老骨头,能替佛祖多护一日是一日……”他忽然停住念珠,望着空荡的佛殿轻叹,“只是不知,当年抄到一半的《金刚经》,后来有没有补全。”
南川缓步走向钟楼,玄色衣袍扫过殿前的香炉,带起一阵细碎的香灰。“开元二十五年,您的弟子慧安和尚,在藏经阁闭关三年,将那部《金刚经》补全了。”他声音低沉,却带着穿透晨雾的力量,“那部经卷现在藏在国家图书馆,卷尾题着‘师恩永沐’四个字。”
了尘大师的念珠猛地顿住,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些微讶异:“慧安……那个总爱打瞌睡的小沙弥?”
“正是。”南川抬手轻叩青铜钟,钟身发出嗡的一声共鸣,震得檐角的铜铃齐齐作响,“他后来成了一代高僧,圆寂前特意嘱咐弟子,要将您坐化的地方辟为静室,日日供奉。”他从袖中取出一卷经卷的拓本,“这是去年寺里翻修时,从静室墙中发现的,是您当年未抄完的手稿。”
了尘大师接过拓本,指尖穿过那层薄薄的宣纸,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欣慰:“这孩子……果然长大了……”他低头看向手中的念珠,那串珠子忽然发出淡淡的金光,竟与魂灯的光晕交相辉映。
令秋将魂灯举到他面前:“跟我们走吧。地府在忘川河畔新建了座禅院,缺位精通佛法的禅师。您去了,既能为迷途魂魄讲经,也能时时听闻这寺里的晨钟——您看,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了尘大师最后望了眼藏经阁的方向,那里隐约透出微光,像是有人正点燃第一盏油灯。他将念珠绕回腕间,身影渐渐被魂灯的光晕裹住:“告诉寺里的僧人,钟楼的木架该修了……莫让晨钟断了传承……”
魂灯被收入怀中时,令秋听见青铜钟忽然自己鸣响起来,一声接着一声,在晨光里荡开层层涟漪。他看向南川,见这位鬼王正望着大雄宝殿的佛像,玄色衣袍在晨雾里泛出柔和的光泽——那是令秋跟随他百年,从未见过的景象。
“王,您似乎对这位大师格外敬重?”
“唐开元二十三年,我来此勾魂时,正遇山洪暴发。”南川转身走出山门,衣袍扫过门楣上的蛛网,“看着他盘腿坐在藏经阁前,任凭洪水没过腰身,手里还紧紧攥着半部《金刚经》。”他顿了顿,望着东方渐亮的天际,“那时候我就想,有些魂魄,本就不该困在阴阳两界的规矩里。”
山脚下传来早课的诵经声,令秋望着怀中微微发烫的魂灯,忽然明白,有些坚守从来不是执念。就像这古寺的晨钟,这坐化的老僧,还有这位看似冷漠的鬼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某样比轮回更重要的东西——或许是信仰,或许是牵挂,又或许,是那份穿越千年依旧滚烫的初心。
晨雾渐渐散去,阳光穿过云层落在寺顶的琉璃瓦上,折射出七彩的光。令秋跟着南川的脚步走出山坳时,听见身后的晨钟仍在鸣响,一声,又一声,像是在为千年的等待画上句点,又像是在为新的旅程敲响序曲。
鬼王令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异世寻缘:空之游戏征途
- 0.1万字9个月前
- 盘龙:龙血武魂
- 地球上的S级王牌杀手苏灿,被最亲之人背叛,本以为生死道消,谁知竟然来到了异世;这里帝国林立,宗门骋驰,这里没有真气,没有斗气,没有魔法,强身......
- 124.2万字9个月前
- 太古遗咒
- 在神秘世界的暗处,一股古老邪恶的力量悄然涌动,它便是太古遗咒。这股诅咒源于上古,曾引发天地浩劫,无数生灵惨遭涂炭。岁月流转,如今它再次觉醒,......
- 5.0万字5个月前
- 正义的理想乡:荒漠之花
- 承接上一部的结尾,正义小队护送夏洛特回约克顿国。本以为超级简单的任务,却在旅程刚开始就遭到了来自敌人的袭击。为了不波及无辜民众,众人经过商议......
- 4.4万字1个月前
- 诡戏人间:鸦夜与他的乐子人剧团
- 顶级魔术师鸦夜在开幕演出中被拖入一场以命为赌注的无限游戏。聚光灯化作血月,舞台沦为废墟,而规则荒诞如噩梦:安抚哭泣的玩偶可能需用谎言折射月光......
- 6.1万字4周前
- 未寄信笺之度假日常
- 来自未寄信笺的番外,主要是讲述主角团一起开心旅游的温馨度假日常~轻松幽默诙谐的语言希望能使大家感到放松
- 0.4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