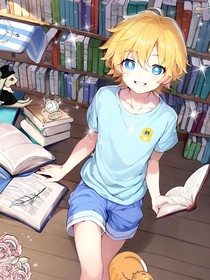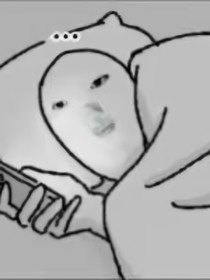《卷三 盲舞》
第三章 舞蹈教室
——在漏水的节拍里,把名字写进骨头
粮站的大门是锈蚀的交响。
贺缘尽用肩膀撞开它那天,铁锈像陈年血痂簌簌落下,
在清晨的光里一闪,像无数碎掉的铜钹。
门轴发出低沉的降E,惊起梁上两只麻雀,
扑棱棱飞向滇南的天,留下一阵高音的颤音。
江愿站在门外,纱布蒙眼,手里拄一根竹杖。
竹杖敲地面,每一下都是试探的弱拍。
“多大?”她问。
“三百八十平米,挑高八米,回声三秒。”
贺缘尽报出数字,像在念一份地形报告。
空气里浮着隔年的米糠味,混着潮湿木头的霉。
他弯腰抱起她,跨过门槛。
脚尖离地那一瞬,她听见风穿过破窗,
像管风琴突然拔了栓,吹出一声低哑的C大调和弦。
“这里以后是我们的教室。”他说。
“也是我们的避难所。”她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粮站内部被一条老旧的传送带一分为二。
前半间,贺缘尽拆下传送带,钉上杉木地板。
钉子每敲一下,江愿就数一下节拍:
“一、二、三、四……”
数到一百零八下,地板铺成,像一块巨大的空白乐谱。
后半间,他保留水泥原貌,
只嵌进四个铁环,吊上两只旧沙袋。
沙袋是部队退役物资,皮面裂口,露出棕黄色的填充物,
像被时间撕开的旧伤口。
贺缘尽用军刀在沙袋上划开十字,塞进去半袋绿豆,
“硬度够,还能发芽。”他笑。
于是,前厅是“芭蕾”。
后间是“防身”。
中间那条传送带轨道,成了楚河汉界,
也像五线谱中间的加线,
把两种极端的舞写进同一间屋子。
漏水的龙头在墙角,
滴答,滴答,
永远慢半拍,
像一位喝醉的鼓手。
招生启事是用红油漆刷在门板上的:
“免费学舞,管饭。”
字歪歪斜斜,像孩子的涂鸦。
第一天来了六个女孩。
最大十五岁,最小八岁,全部来自镇上的留守家庭。
她们穿着塑料拖鞋,脚趾上沾着田里的红泥。
江愿让她们把脚洗干净,
再排成一列,手扶把杆。
把杆是一根竹竿,横架在米仓的梁上,
摇摇晃晃,像随时会跑掉的音符。
退役的缉毒犬叫“黑耳”,七岁,
左耳被弹片削去一半,听力却比谁都灵。
它趴在门口,尾巴一下一下拍地,
把节拍器漏掉的半拍补齐。
第一节课,江愿教“一位”。
她看不见,就用手掌量孩子们膝盖的缝隙。
“并拢,像冬天挤在一起取暖的鸟。”
孩子们笑,她也笑,
笑声撞在杉木板上,发出柔软的回响。
后间,贺缘尽教“直拳”。
他让女孩们把拳头抵在沙袋上,
“想象袋子里装着你最怕的东西。”
十五岁的阿兰把额头抵上去,
眼泪滴在绿豆缝里,
第二天沙袋就长出第一株豆芽。
黑耳负责秩序。
谁偷懒,它就低吼;
谁动作标准,它就舔那孩子的脚踝。
狗舌头粗糙,像一块会动的砂纸,
把孩子们的恐惧磨平。
满月那天,粮站里来了位纹身师。
是个哑巴,背包里装着一次性针头和自制墨水。
墨水用锅底灰、白酒和甘蔗汁调成,
黑里透甜,像烧焦的糖。
江愿先躺上床板。
右脚踝内侧,皮肤薄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
纹身师用碘酒擦过三遍,
针头落下时,她听见自己心跳放大成鼓。
“HJY”三个小写字母,
像一串低调的音符,
藏在踝骨后面,
只有她抬腿做 arabesque 时才会露出来。
贺缘尽纹在左肋。
皮肤贴骨,针头每进一次,都像敲在琴键最深处。
“JY”连笔,
像一支弯曲的鹤颈,
又像子弹划过的弹道。
纹身师问要不要麻药,
两人同时摇头。
疼,才记得住。
疼,才能把名字写进骨头,
而不是写进皮肤。
江愿的伤口渗出血珠,
她用指尖蘸了,点在黑耳鼻尖。
狗嗅了嗅,尾巴摇成四四拍。
七月十五,台风过境。
雨像倒翻的墨汁,
把粮站屋顶砸出无数细小的鼓点。
夜里十点,教室断电。
孩子们早被家长接走,只剩他们两个。
江愿站在前厅中央,
赤脚踩在木地板上,
雨水从瓦缝漏下,
在她脚背汇成一条细小的溪流。
贺缘尽从后间走来,
手里握着半截蜡烛。
火苗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像他们这一路飘摇的命。
他把蜡烛放在地板上,
雨点落在火苗旁,
“滋”一声,
升起一缕白烟。
江愿抬手,
指尖顺着他的眉骨滑到唇峰,
像在读盲文。
然后她踮脚,
足尖点在雨水里,
发出“啪”一声轻响,
像乐队里的 castanet。
吻落下来,
带着雨水的凉和血的腥。
他们的舌尖碰到半枚子弹的金属味,
那味道让他们想起第一次拥抱——
在医院走廊,
子弹还嵌在他肩胛,
她抱着他,
像抱住一支走音的笛子。
雨越下越大,
蜡烛终于熄灭。
黑暗里,
他们的心跳变成唯一的节拍器:
咚——咚——咚,
每一下都在确认:
你还活着,
我也还活着。
台风过后,
粮站门口多了一架旧钢琴。
琴键缺了三个,
音色却意外地温柔。
江愿每天清晨坐在琴前,
弹《月光》第一乐章,
用左手补右手,
用身体补声音。
贺缘尽把孩子们分成两组:
一组练芭蕾,
一组练拳击。
黑耳在中间跑来跑去,
尾巴打在地上,
像指挥棒。
夜里,
他们在地板中央躺成十字。
天花板上的裂缝像五线谱,
星星是音符。
江愿说:
“如果有一天我先走,
就把我的骨灰掺进墨水,
给孩子们的足尖鞋上色。
这样,
我就能继续跳舞。”
贺缘尽笑,
笑得胸口发颤:
“那我就把半枚子弹熔成纽扣,
钉在他们练功服的领口。
这样,
他们每转一次圈,
都会想起我们。”
纹身师留下的最后一点墨水,
被他们用毛笔蘸了,
在粮站的外墙上写下:
“疼,才记得住;
记住,才配活下去。”
字歪歪扭扭,
像孩子的舞步,
却像誓言一样,
钉进风里,
钉进雨里,
钉进每一个留守女孩和黑耳的梦里。
舞蹈教室的灯,
从此不再熄灭。
是败笔,亦是绝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请弯道超车
- 是改版。这次是以故事主线发展的连续小说。新人祝您食用愉快,老顾客请您包容。狗血逗比,人设崩塌文。看这本书不用正经。
- 2.7万字9个月前
- 苏三:喜欢你
- [拆香苏土豆原创女主]
- 2.0万字9个月前
- 可是他叫我达令
- 自力更生的大学牲江陵一VS纯情可爱的小人偶木傀。——————木傀是个小人偶,他总是像个孩子一样,直率地表达着自己的欢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 2.0万字7个月前
- 烬之歌
- 三神余一,邪祟作乱。血统的改造,亲人的秘密灾厄的真相,父母的离去人性与神性的抉择……这是作为『序者』,作为神明候选人的她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她......
- 1.8万字6个月前
- 熠楚
- 猜猜看拥有马甲和幕后黑手的是谁呢~一位算计满满的杀手和一位实力强大的经济家由于某些原因,导致许楚辞在少年时期霸凌了许熠星,从此一段故事就此开......
- 2.1万字4个月前
- 地下电竞王逆袭全网跪求我收手
- KPL别看我光鲜亮丽站在聚光灯下,其实我以前打过“野赛”。所以经常有人问我:“哥,电竞圈真有打假赛、开赌盘这种事吗?”有,但绝不是小说里写的......
- 1.6万字2个月前